我的家鄉在河北陽原。
在我的印象中,家鄉既沒有歷史悠久的名勝古跡,也沒有享譽天下的民俗特產👩🏻🦯➡️,因而也就鮮有人知道。最沾得上名人邊的,也許就是大作家丁玲和她那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了,因為桑乾河就在我家鄉那一帶👁🗨。書中描寫的“谷子又肥又高,都齊人肩頭了。高粱遮斷了一切,葉子就和玉茭的葉子一樣寬🙍🏽♂️。泥土又濕又黑。從那些莊稼叢裏,蒸發出一種氣味”的情景,依稀有些印象,但更多的兒時的記憶卻是母親在貧瘠的土地上艱辛的勞作以及那一日三餐賴以充饑的沙沙的能煮開了花的山藥蛋和粗粗的橙黃橙黃的玉米面餅子了,和小夥伴們擠在一起曬太陽的時候便幻想著天堂的日子大概就是頓頓能吃上白面做的饅頭吧。
但是👨🏿🚒,最近這幾年,我的家鄉卻突然因為“泥河灣”這個名字而蜚聲中外了🧗♀️。因為考古界在家鄉的泥河灣發現了大量舊石器和哺乳類動物化石,泥河灣也被國際學術界標定為第四紀地層(即從260萬年前到現代)代表地點,其研究價值可與世界公認的人類起源地:東非的奧杜維峽谷相媲美😷。泥河灣遺址的考古發掘被評為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泥河灣遺址群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仿佛一夜之間,泥河灣🚈,這個河北省陽原縣的小山村👩🏻🏫,成了“神秘📌、寶地。”的代名詞📄🍏,被冠以 “中國泥河灣”🕉👩🏼🍼、“中國陽原泥河灣”。😆🤷🏽!

最早發現泥河灣具有考古價值的還是早在1921年來這裏傳教的外國神甫。也許是上帝的昭示、天主的惠顧,這位神甫在傳教之余閑暇遛彎之間,竟在村周圍發現了大量貝殼🤿、蚌類和哺乳動物化石🪱,並以他的知識判斷🚶♂️,這裏的地質地貌也非同一般。在他把他的發現告訴了同在中國傳教的法國古生物學家之後,引起這些外國專家們的極大興趣🚵🏿♂️🏋🏽♀️,由此也拉開了泥河灣考古發掘的序幕。
令舉世震驚的是,隨著科學有序的發掘😓,泥河灣以她獨特的古地層和出土的化石、石器竟展現出了一部人類進化的宏大歷史畫卷! 200萬年的馬圈溝遺址🐰👩🎨、136萬年的小長梁遺址👨🦼、100萬年的東谷坨🍈、岑家灣遺址🤸🏽♀️🧑🎤、78萬年的馬梁、雀兒溝遺址、10萬年的侯家窯、漫流堡遺址、1萬年的虎頭梁遺址、5000年的姜家梁墓葬群🧍♂️。🏊🏿♀️,這些熟悉的家鄉鄉鎮村落的名稱竟和古人類的進化史一一聯系在了一起🚴🏼🧔🏿,怎不令人興嘆!據說,泥河灣遺址發掘出的最具價值的文物之一是一件燧石刮削器,奇妙的是這件刮削器恰巧置於一條大象的肋骨上,且周邊散落著許多明顯有刮削痕跡的肋骨和可用於刮削的石片等。於是現代人據此展開了豐富的想象,把這一場景描繪成了一幅祖先們在“遠古人類的餐廳”饕餮大象的“人類第一餐”。更加令人驚嘆的是,這些祖先們用過的隨手放在“餐桌”上的“餐具”,竟把泥河灣盆地的舊石器年代向前推進了數十萬年,把亞洲的文化起源提前了超過200萬年!難怪學者們大膽推斷:人類不僅從東非的奧杜維峽谷走來,也從中國陽原的泥河灣走來!

家鄉有了如此重大的發現👱,自然得慕名前去瞻仰一番。於是利用放假回家探望老父親的機會,選了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約了依然在家鄉工作的哥哥一道前往泥河灣遺址。雖然我們開的是一個底盤較高的皮卡車,但依然一路崎嶇顛簸,顯示出拜謁古人類遺址的不易。在經過了一座由威武的大象和兇猛的犀牛以及它們的牙齒構建的大門一樣的標誌性建築後,我們終於進入了“古人類的村落”👱🏼♂️。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巨大的古人類頭像的雕塑🦻,外貌酷似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頭顱,但在這裏被雕塑家加上了一頭濃厚飄逸的長發,顯得更加悠然俊秀,在陽光的照耀下傲然註視著前來瞻仰的後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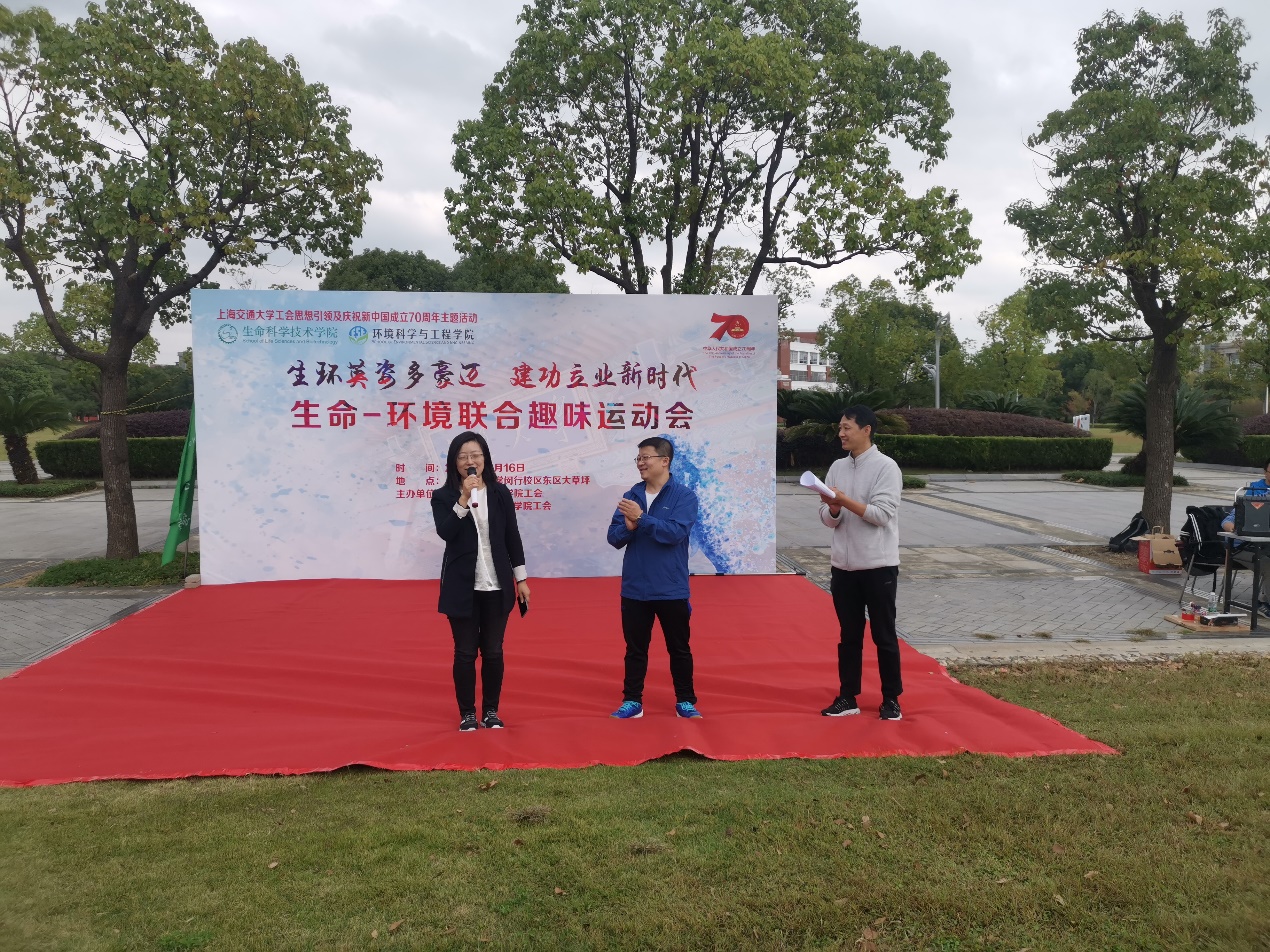
站在山坡的高處👶🏻,俯瞰泥河灣遺址,滿眼的是那層層疊疊、縱橫交錯的山丘和溝壑,間或分布一些大小不一、錯落有致的臺地。那些顯然是人工挖掘的整齊有序的巷道串聯在山丘之間。眺眼望去,遠處似乎還平鋪著一個很大的平原一般的谷底。這裏沒有豎起我想象中的大規模的保護性建築,也沒有電視裏常看到的那些帶個小錘、小鏟在現場挖掘的考古工作者🛀。我努力地在想象我們的祖先們在這裏生活的場景,恍惚間仿佛那層巒疊嶂的山丘變成了古人類的城堡,而那平坦有致的巷道便是城堡間的“交通要道”了。看來真是隔行如隔山,我這個說起來也是從事環境研究的人,也實在看不出其中的奧妙,肉眼凡胎😥,只能閉目遐想了🎅🏽。

還是現場展示的文獻資料幫忙解了惑🧔🏿,原來早在200多萬年前🎣,這一帶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有茂密的叢林🪳,廣闊的草原🕙,還有一個水域面積達到9000多平方公裏的偌大的湖泊。大湖四面環山😑,煙波浩渺🫄,湖水清澈,魚蚌不驚😇,成為了古生物的樂園!在這百花爭艷,充滿生機的原生態地域👨🔬,我們的古人類也就伴隨著從最早的生命體單細胞生物到海藻類微生物🙎🏿、從無脊椎動物到脊椎動物、從水陸兩棲的哺乳動物到恐龍等爬行動物、最後到靈長類動物猿類的生命和人類的進化史一路走來!相對於地球已長達45億年的高齡,200萬年不過是彈指一揮🚿。然而就是這彈指一揮間,實現了從爬行到直立、從模仿到思維🧔🏻♀️、從原始狩獵到製造工具的質變和飛躍!這東方古人類由猿到人的偉大飛躍就是在我眼前這塊看似貧瘠的土地上蟬變升華的嗎?站在這片在蒼涼的地表下由層層土質和片片化石記錄了人類進化史的遺址古跡面前,我不禁湧起一種登高臺而“念天地之悠悠🫶🏿。”的感慨🚌!
星轉鬥移、滄海桑田🤦🏼♂️。大約在1.8萬年前,由於第四紀冰川期劇烈的氣候變化和地殼運動,導致這一帶湖底上升🧟♀️,土體交錯,那孕育了東方古人類的大湖也逐漸流失幹涸,露出了寬廣開闊的平原,逐漸形成了今天綿延起伏的丘陵和溝壑🐂👩🍼,也將那猛獁大象的遺骸以及祖先用過的石片、石球深埋地下,只留下桑乾河依然用她那並不豐裕的水流吟唱著沉澱了百萬年記憶的古老歌謠🏄🏽。天哪😴,原來如此!何時日月輪回、乾坤翻轉🤸,再把那浩瀚大湖還我家鄉🧗🏻!重現天人合一🪈、萬物興榮的生態樂園🤵🏽♂️!
記得第一次帶我妻兒回陽原老家省親🙍🏿,好奇的女兒問我🥷🏻:“陽原”這個名字是從哪兒來的?我隨口答道:也許是祖先們以為這裏原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故起名為“陽原”吧。這明顯帶有虛榮和忐忑的杜撰,年幼的女兒居然信了,未再追問有何出處或依據。今天,那被發掘出的深埋在地下的泥河灣的故事🧏🏻♀️,科學雄辯地向世人昭示🤾🏻♀️:這裏就是東方人類的祖先最早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一種發自心底的對家鄉的自豪和驕傲在那濃濃的故土情懷中冉冉升騰,這自豪難以言表👲🏻,這驕傲無法謙虛!
啊🕵🏿♂️,我家鄉的泥河灣🌛🤳。
何義亮
2013年2月於上海
筆者白描:
何義亮🧑🔬😋,意昂4体育平台教授,工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水汙染控製設計研究所所長。2006年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訪問教授💆🏼♀️,2003年日本國立歧阜大學訪問學者。
